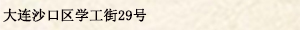家乡故事对廊坊名称由来的粗浅思考
对廊坊名称由来的粗浅思考
缴世忠(缴氏家族二十世)
有幸参加廊坊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的廊坊地名由来研讨会,感到很高兴,这是向在座师友们学习的好机会。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廊坊名称由来的两种说法,我是一个局外人。即不是“侍郎房”说的参与者,也不是“琅珐寺、马奉经(蜂精)”说的参与者。初时,对二者均未留心在意,仅仅是浅层次的感到“侍郎房”的说法很突然,以前从没听说过;而对于“琅珐寺、马奉经(蜂精)”的说法感到很别扭,好端端的一个廊坊和一个违法犯罪的流盲和尚联系到一起,我是真心实意地替廊坊“坐地户”的人们感到憋屈、窝囊、无奈。这不过是当时掠过的一种感觉。没有深思熟虑,更没有仔细辨别和考证。
年9月,应市地方志办公室聘用,负责县(市、区)志编审和指导。年4月,迁居安次区新新小镇。十几年来,选读和查阅了《二十五史》《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日下旧闻考》《畿辅通志》《河北通志稿》,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民国《安次县志》,岳一中《廊坊史话》,《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汉语大词典》等等史志书籍和工具书;也在休闲聊天时作了一些让对方毫无察觉的“民意调查”,算来仅仅问过20个人,面很窄,不足为据,但也算是一个小范围的反映吧。这20个人中,有8个人不知道,或不关心,或认为无所谓;10个人认为当然是“侍郎房”的说法好;2个人表示听到过“琅珐寺、马蜂精”的说法,认为如果是有据可查的实事,也不能回避。下面向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与会师友们汇报我对廊坊名称由来的粗浅思考。
一、地名的意义和功用
地域名称,是县以上各级民政部门管理的事务,与地方志、党史、政协文史资料等机构的业务有着紧密地联系。同时,也是地名聚落内较有文化素质的居民关心和感兴趣的事物。我们这些长期坐机关忙公务的人,讨论研究地名由来,似以首先弄清楚地名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用为宜。
㈠地名是梦归故里的牵挂
地名,满满承载着地域的春华秋实、暑往寒来。它标示的古老称谓和蕴含的地理信息,启人心智,经久不衰,或铭记人心,或载入史册,深深镌刻在人们记忆的深处。不论走到天涯海角,还是踏进异国他乡,家乡地名都是人们梦归故里的心底牵挂。
㈡地名是一部丰满的史书
地名,忠实刻录着悠悠岁月的万事万物。尘封已久的史迹,不时钩沉出来散发出浓郁的芳香,让我们聆悟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先民繁衍生息,渐成聚落的艰辛。地名就像一幅家谱,一套县志,一部国史,传至千秋万代,也一直是人们心目中不可替代的丰满史书。。
㈢地名是厚重的文化自信
地名,传承着血缘与根脉,折射着社情与民意,积淀着文化与睿智。遗址的发掘,文物的出土,民俗的演变,家训的沿袭,乡规民约的修订,都是民间文化的瑰宝,历史文化的化石。古往今来,地名始终是“精气神”“创业史”“福满地”的展示,是厚重的民族文化自信。
㈣地名是人们博大的情怀
地名,浓缩并孕育着深厚的情愫。有备受敬仰的先哲名人,也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交融。地名之下的行行翠柳,袅袅炊烟,阵阵蝉鸣,潺潺河水……人们的思念,都默默珍存于地名之中,不离不弃,不馁不躁地静静守候着,蕴含着中华民族坚韧的志向和博大的情怀。
㈤地名是人们的永远记忆
地名,时刻活跃在人们的思维中。离乡赤子难忘父老乡亲在街口送行、又盼望归来的深情。家乡的一条老街,一株古槐,一口水井,一台大戏,一道花会,一条车道,一处坑塘,一洼油绿,一片金黄,一园青菜,一树桃李,一地西瓜……都是人们最深最美的永远记忆。
二、“侍郎房”说的思考
《廊坊市志》(以下简称市志)第一卷《概述·一》第1页第2自然段记曰:“‘廊坊’由来已久。早在一千多年前,安次人吕琦(宋朝宰相吕端之父)在后晋做兵部侍郎。吕琦在家乡建一庄园,园大房高,远近闻名,被当地人称之为侍郎房。久之,侍郎房成为村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为了叫着方便,便叫成郎房。19世纪末,京山铁路经过郎房,车站将站牌名称写成廊房。这样,廊房从此为外界所知。建国后,当地人为书写方便逐渐将廊房写成廊坊。”
㈠应当肯定的3点
1.史上确有吕琦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年版《二十五史》拼缩影印十二卷本第六卷《旧五代史·九二·晋书》第一四一页第1~2栏《吕琦传》。
2.确有北宋宰相吕端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年版《二十五史》拼缩影印十二卷本第八卷《宋史·下》第一○六八页第3~4栏至第一○六九页第1栏《吕端传》。
3.“侍郎房”与“郎房”吻合
市志所记“被当地人称之为侍郎房。久之……便叫成郎房。”其“待郎房”“郎房”的称谓,与清乾隆《东安县志》卷二《建置志》第八页所记之“东北路—郎房—离城三十里”的称谓,相互吻合。
㈡两点存疑或无史证
1.吕琦建庄园无史证
市志所记“吕琦在家乡建一庄园,园大房高,远近闻名”,在《晋书》第一四一页第1~2栏《吕琦传》中没有记载,在所有东安、安次县志中没有记载,也没有发现涉及此事的野史、谱谍。似可初步认定这一记述缺少史实佐证。
2.廊房村名始于何时
市志记载始于五代后晋。但是,查康熙《东安县志》卷二《乡村》记载的全县个村庄中,没有郎房村名。到乾隆《东安县志》卷二《村庄》记载的全县个村庄中,才出现了“东北路—郎房—离城三十里”的记载,证明清康熙十二年(年)以前还没有“郎房”这个村名。那么,郎房村名始于后晋,就缺少直接的史实佐证。
三、“马奉经、琅珐寺”说的思考
此说始见于岳一中老师编著的内刊号“LN”资料书《廊坊史话》。此书第3—4页写为“廊坊是原东安县的一个小镇。追溯到它的建立,将近百年,原来只有近20户的廊坊村,该村始建于明初。那时,在现在木柴库附近建起一座寺院,名叫琅珐寺。永乐2年(公元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来侯安、候敖兄弟2人,在寺院附近住了下来。后来随着迁民的增多,使这里逐渐形成一个小村落。叫什么村名呢?经过人们议定,干脆就用寺的名称命名叫琅珐村。到明朝末年,村民的生活还算过的去。可是,寺内和尚横行不法,经常去京都作案,扰乱民安,屡有告状的,官府为铲除这一祸害,探知是琅珐寺和尚所为,便派兵捉拿马奉经。但马奉经闻讯却逃跑了。官兵没有捉到人,则把琅珐寺烧毁。村里人为躲避嫌疑和灾祸,纷纷外迁,大部分都搬到北头地里盖房居住(今市工具厂东北角上)。由于琅珐寺被焚,人们觉得用寺名起的村名不吉利,于是就取其谐音改称郎房村。”
第6页写为“廊坊出现于明朝初年,原名琅珐,因村庄附近有琅珐寺而得名。
后来,琅珐寺被毁,又因用字生僻,取其谐音叫郎房,后又改成廊坊。
清乾隆十四年(公元年),廊坊作为一个小村收录于《东安县志》。这是最早的文字记载,距今已年。“
㈠应当肯定的3点
1.传说、故事是民间文化
应当肯定这是一则民间传说,或者是一则民间故事,岳一中老师采访记录下来,供大家做为聊天的话题,为廊坊民间文化增添了一则追根溯源的地名故事。做为传说、故事,有的与史实相合,有的似合非合,有的与史实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做为民间口头文学,不必苛求史证或史志记载。更不要把传说当做史实
2.传说中“郎房”与县志记载相合
此传说中说的“改称郎房村”,与乾隆《东安县志》记述的村名相合。
3.认同乾隆志的记述
传说中引用了清乾隆《东安县志》最早记述的“郎房”村。
㈡若当作史实则没有史证
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很多是平民百姓依据自己的阅历顺口讲说,逐渐凑成的一段段小笑话。例如“说笑话,道笑话,灶火坑里爆爆花。先爆一捧金,后爆一捧银,再爆爆出个聚宝盆。聚宝盆里胖小子,摇身变成小伙子。小伙子,长的好,娶了个媳妇叫香草……”还有什么“一家子,两口子,生了个孩子叫水斗子。水斗子,水量大,扎蒙子扎到河底下。连阴天,河水满,大伙上堤去护险,水斗子下河找漏眼。一蒙子扎到龙华桥,拐回来又到十里湾,焦家口、杨家口、王家口,一直查到西河沿……”此类传说、故事,一般是旧时闲谈聊天的话题,只反映一个时段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一般不能做为史实去考证或运用。
同样,如果我们把“马奉经、琅珐寺”的故事传说当做史实诠释廊坊地名的由来,那就得和“侍郎房”说一样,经受史证和史志记载的考量与验证。
1.史志均无“琅珐寺”记载
查康熙《东安县志》记述祠4座、楼1座、坛3座、寺庵观院庙宇56座,没有琅珐寺之名;乾隆《东安县志》记述坛3座、寺庙54座,也没有琅珐寺的记载;民国《安次县志》以及相关书籍,都没有“琅珐寺”记载。而“琅珐寺”传说也只是指说了一个地点,但一直没有虚墟、遗址、座向、建筑规模等最基本的信息。传说故事嘛,茶罢饭余闲谈海论,没有必要用史实的基本要素去论证。所以,琅珐寺这种属于没有史证的故事传说,不能做为史实写入志书。
2.马奉经其人查无史载
传说故事中的违法犯罪流盲和尚马奉经,在一些故事版本中被谐音为“马蜂
精”,均属于查无史证、没有文字记载的故事传说人物,既然没有任何史证,那就不能做为史实写入志书。
3.建村时间自相抵牾
“马奉经、琅珐寺”说中始见“郎房”村名,先后有3个不同的时间。
⑴“追溯到它的建立,将近百年”;(《廊坊史话》第3页第一节第1行)
⑵“该村始建于明初……永乐2年(公元年)……”(《廊坊史话》第3页第一节第2—4行)
⑶“清乾隆十四年(公元年)……距今已年。”(《廊坊史话》第6页第二节倒2至末行)
在短短4页中,就出现了3个始见“郎房”村名的不同时间。做为传说故事一般也会顾及前后一致、自圆其说,避免自相牴牾,矛盾频出;而想要当做史实运用的这个“马奉经·琅珐寺”说,怎么能够这样明显地自相抵牾呢。
4.传说与县志记述相差年
“马奉经、琅珐寺”说,说是郎房村始建于明永乐二年(年);而郎房村记载始见于清乾隆十四年(年),前后相差年。如果把这个“马奉经·琅珐寺”说当作史实诠释廊坊名称由来,这年的差距怎么勾销呢?
5.传说情节不合常理
传说中关于“村里人为躲避嫌疑和灾祸,纷纷外迁,大部分都搬到北头地里盖房居住(今市工具厂东北角上)”的说法不合常理。既然是“寺内和尚横行不法,经常去京都作案,……官府……探知是琅珐寺和尚所为,便派兵捉拿……官兵没有捉到人,则把琅珐寺烧毁。”一方是官府、官兵,一方是不法和尚,没有涉及平民百姓,能有什么嫌疑和灾祸呢?凭什么村民“纷纷外迁,搬到北头地里盖房居住”呢?既非兵燹匪患,也不是大火连天,又没有因为和尚犯罪而株连村民,实在没有理由“纷纷外迁”。有人会问,你老头怎么知道没有“兵燹匪患,大火连天,和尚株连村民”呢?这不在于我知道不知道,而是传说故事里根本没有这些情节。那末,这个不合常理的村民“纷纷外迁”,整个村子都迁移了位置的说法,就只能当做笑话说说,而不能当成史实让人相信了。
6.“珐·房”谐音不是廊坊方言
传说中说是取谐音把“琅珐”改为“郎房”。谐音,并不是“大估摸、大概其、差不多、好像是”之类的随便一说的事情;它是涉及《音韵学》和《语音学》基本常识的语言音韵现象。
琅、郎古今读音相同。
珐、房古今读音均不相同,不能谐音。
珐,古时弗泛切音,姂洽韵,读为fà(髮音),属于去声。
房,古时符方切音,防阳韵,读为fánɡ(防音),属于阳平。
以上是“珐、房”的古时读音。在现代汉语里,原安次县北半部即现在廊坊市区及以北的方言很接近普通话发音。人们对于“琅珐、郎房”这对名词中的“琅”与“郎”读音相同,都读为lán(廊音),不存在谐音的说法。节点在于“珐、房”能不能谐音。
珐字古时读fà(髮音)。发音时,先发f声,即上齿触下唇形成窄缝,让气流从缝中挤出,摩擦成声;后发à音,唇自然张大,舌放平,舌面中间微隆,声带颤动,发出完整的fà音。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理髮、美髮、髮型、白髮苍苍”等词语中的“髮(fà)音”,属于唇舌音。
在现代汉语的廊坊方言中,一些人把“珐”读为fǎ(法),由古时的去声
变为上声,而讲究语音和音韵的人们仍然读为fà(髮音)。
房字古今读音相同,均读为fánɡ(防音)。发音时,声母f发声与“珐”同;韵母ánɡ发声时,先发ɑ音,然后舌根抵住上软腭,让气流从鼻腔泄出,发后鼻音尾nɡ音,此属唇鼻音。
做为很接近普通话的廊坊市区及以北区域的方言,发音清楚,声、韵准确,不可能把“珐”这个唇舌音(fà或fǎ)谐变为唇鼻音的“房”。这如同廊坊人不可能把“方法”读成“方房”,把“办法”读成“办房”,把“头髮”读成“头房”,或者是把“房子”读成“髮子”“法子”,把“国防”读成“国法”,把“妨碍”读成“乏碍”等等。如果说确有这种“ɑ、ɑnɡ”韵不分的方言存在,那么要到晋、陕、甘、宁地区去找,在廊坊是不会存在的。所以,说“琅珐”谐音成“郎房”不符合廊坊方言实际,是不能成立的。
四、两相对比后的取向
我做为局外人,依据史志记述和客观实际,对以上两种说法做了粗浅的思考和分析对比之后,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看法,谨供市地方志办公室参考。
㈠“侍郎房”说史证不足
此说尽管吕琦、吕端国史有传,县志有载,其“侍郎房——郎房”之说也与清乾隆《东安县志》记载的“郎房”村名相符合。但是,如果严苛的考证,吕琦建高大宅院没有史志记载,从吕琦建宅到清乾隆《东安县志》修成的多年,郎房村也不见史志记载。似乎认为是史证不足。在这里使用“严苛”“似乎”,是因为历代名人传记一般只记到县级出生地或籍贯,而很少有记述传主是哪个里、哪个村的人,更没有修建宅院的记述,至于传记印刷出版以后漫长岁月里,传主出生地村名的沿革,更不可能一一见诸于史志记载。所以对于苛求之下的结论只能用“似乎”表述。但不宜轻易定论为“杜撰”。
㈡“马奉经、琅珐寺”说根本没有史证
此说仅仅是以候氏兄弟为起源的民间故事传说,马奉经其人、琅珐寺庙宇,既不见于任何史志著述记载,又没有本原的侯氏家谱、家账佐证,也没有遗迹、文物、寺庙形制规模等实证。故事传说,讲说的再形像、再具体,也仅仅是故事传说,为史志者实在不能拿了故事传说当历史,这属于史志工作的一般常识。所以,此说不能做为廊坊名称由来的依据。
㈢从精神层面考量
没有任何史志记载的琅珐寺,尤其是那个没有任何史志记载、为非作歹、违法犯罪的流盲和尚马奉经,是从古至今人所不齿的败类形象,如果史志记载确有其人,那也回避不得,应当承认史实。但是,这个败类形象根本不见于任何史志书籍记载,仅仅是一个民间故事性的传说,为什么非要和这种不一定存在的败类形象联系到一起呢?和他联系到一起,对于廊坊人,除了叹息、无奈、憋屈,能有什么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作用呢?对于廊坊人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热爱家乡,振奋精神,勇于担当,又有什么鼓舞和激励作用呢?
廊坊地名和吕端联系上,有什么不好啊?第一,吕端的确是廊坊人;第二,他是北宋时期为国为民的著名宰相;第三,毛泽东主席曾对叶剑英元帅说过“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宣传吕端,提高廊坊知名度,以利于招商引资,助推廊坊发展,又有什么不好呢?吕琦是后晋四部侍郎,其子吕余庆、吕端都是北宋初期宰相,他们两代人都饱读诗书,学识渊博,治国理政,功绩卓著,是原安次县域古时五位宰相中的佼佼者。联系上这样本乡本土的名人、好人,鼓
励廊坊人奋发进取,为国为民,勇于担当,会有什么不好呢?
㈣感谢毛志刚先生的建议
拜读了广阳区毛志刚先生的建议书,很受感动。十分感谢毛志刚先生对地方志、对廊坊名称由来的关心。如果我们廊坊市能够有更多这样关心地方志事业的人士,不断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由市地方志办公室汇集起来,分门别类,综合梳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以指导和辅助地方志工作。我们廊坊市地方志事业必将稳步提升工作质量,不断推出优秀成果。
㈤几个具体提法的商榷
1.“侍郎房”源头与称谓
市志所载,修建“侍郎房”的源头是后晋时期的四部侍郎吕崎,而不是北宋宰相吕端。是“侍郎房”,而不是“令郎房”。
2.关于“真实来源”的提法
把既没有史志记载,又没有谱谍佐证,也没有实物(碑铭、砖瓦、佛具、寺庙座落布局图等)实证的“马奉经、琅珐寺”的故事传说当做廊坊名称的“真实来源”,明显不符合“最具可靠性的史料莫过于《县志》”的定论。如果都把故事传说当做历史,那么古今档案、历代文物、各级各地史志著述还有什么用处?当然,不能排除档案、文物、史志中有舛误和瑕点,也不能否定某些故事传说中的真实性。但是,从古至今的历史毕竟是以档案、文物、史志著述为准的。毛志刚先生在建议书中强调的“最具可靠性的史料莫过于《县志》”“一部是康熙志,一部是乾隆志,在两部县志中均未找到‘令郎房’一词的记载,也就是说从宋朝到清朝四百多年根本就没有令廊房村的存在”。由此断定“侍郎房”的说法是杜撰。那么,用同样的标准考量不见于任何史志记载的“马奉经、琅珐寺”的说法,又该做何定论呢?如果否定了“侍郎房”说法,把“马奉经、琅珐寺”的说法当成廊坊名称的“真实来源”,这显然是双重标准的不公正主张了。
3.吕端是哪个村的人
曾有人说过,吕端是市区王寨人,但是没有佐证,只能存档备查,不能做为史实记述。至于提出吕端是后屯人,不知有什么史证。若仅是一说,同样不能做为史实运用。
4.“火车拉来的城市”与地名由来
我很欣赏“火车拉来的城市”的提法和文章,它从一个方面叙述了廊坊城市建设的历程,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外界还有“廊坊市是京津二市扶持起来的”评论,史志界也有“廊坊市是廊坊人民奋斗出来”的说法。不论是哪种说法,其主题思想都是表述的廊坊城市建设历程和成就,与廊坊名称由来没有关系。不必把无关内容插入地名由来论题中讨论。
5.廊坊名称由来的措置
既然在严苛要求下认定“侍郎房”说史证不足,那就把它降格为一种传说。如果说降格到传说也不行,那就有“唯我独好”之嫌了。我们拿了这个“侍郎房”传说与“马奉经、琅珐寺”传说相比较,何优何劣,孰好孰差,此前已辨别得清清楚楚,不再赘言。建议:市志“侍郎房”说不必更改。第三轮修志启动在即,届时在廊访名称由来之“侍郎房”说前增补“相传”二字,而后再附录这次研讨会纪要或有说服力的文章,给廊坊读志用志人一份认真的答卷就可以了。
以上仅仅是一个局外人的粗浅思考,不当之处,敬请与会师友指正。
缴世忠
年7月9日于廊坊市安次区新新小镇
缴世忠:男,河北省方志学会会员。年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缴河村(二十世)。曾在大城县人民武装部任干事,参谋等职。年转业到大城县县直武装部任部长。年自学考试中文大专毕业,年中国人民大学方志专业证书班毕业。任大城县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大城县志》常务副主编,职称副编审。被《中国当代方志学者大辞典》录入。他是河北省方志学会会员,《方老研究》和《黑龙江史志》特约记者。一九八六年开始从事地方志的编纂与研究,主要编著有《大城县志》撰稿14万字,审修80万字(已出版)发表文史志文章篇,其中方志论文40篇。
点击以下链接,详见具体作者介绍:
史志编纂——缴世忠
扫一扫更精彩: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