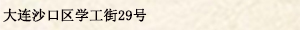王顺友这个曾经全中国最孤独的男人,解救了
封面图|源于寻访纪实节目《闪亮的名字》
青鸟是一只传说中的鸟。
它会为人们带来幸福和希望。
它没有脚,只能不停地飞,唯一的一次着陆,就是死。
王顺友就是那只青鸟,他在雪域高原上奔波半个甲子,只为解救那群屏蔽在时代之外的人们。
他是那片土地上最忠诚的使者。
他从未停歇,直到死去。
随着他的离开,一个时代也跟着结束了。
年,19岁的王顺友接过父亲的邮包和骡马的缰绳,穿上绿色制服,成为他们家里第二个邮递员。
交接时,父亲告诫他:“不能丢失邮件,不能打湿邮件,不能托人代收,不能贪污邮件。”
王顺友把这四句话刻在了骨子里,终成了木里“马班邮路”上最忠诚的使者。
而他第一次邮递的经历让他记了三十多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这片高原深山里的人们需要看到外面的世界,也需要被外界“看到”。
8月,天上似乎被劈开了个口子,暴雨倒灌,部分地方已经出现了泥石流。
对于王顺友要走的这条路来说,山体滑坡随时而至,但他还是没有停下邮递的脚步。
因为这次的邮包里有一封大山女孩的录取通知书,大山里的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可大学报到时间不等人,王顺友无论如何也要把通知书准时送到。
那次的邮递路,每天都下雨,王顺友拄着一个从树上掰断的枝干,可还是因为路面太滑,摔在泥坑里无数次,身上的雨衣也早变成了破旧不堪的“泥衣”。
等到王顺友历尽万难把通知书送到女孩家的那天,才发现这个未来的女大学生正在办婚宴。
她和同村的男孩被父母订下了娃娃亲,等女孩高考完,就结婚。
读书对于一个大山的孩子来说有多重要,在这里,或许只有王顺友明白。
他告诉女孩:“现在结婚太早了,你这个年龄应该去读书的。”
“我以为自己没考上......",女孩的脸上有对未来的迷茫,有考上大学的欣喜,也有即将成为人妻的害怕。
“娃,听叔的话,先去读书吧。”王顺友不想让这个女孩一生困在这座大山里,明明她可以有更光明的未来。
女孩答应了,但村民不答应:她去上大学了,谁来生孩子?
男孩的父母愤怒地看向王顺友,“是我们儿子重要,还是大学重要?”
“当然是大学重要。”王顺友明白,正因为这群人知识贫瘠,才让他们强迫一个未来的大学生在十几岁就嫁作人妇。
男孩的父母和亲戚开始推搡辱骂他,他们认为王顺友是阻碍自己儿子婚礼的绊脚石。
平时好脾气的王顺友在这会变得又轴又硬,他必须要让女孩去读大学。
最后,男孩的父亲逼着王顺友写了一封保证书,要他保证:等女孩大学毕业后,马上回到这个村子里和他家儿子结婚;以及女孩在读大学期间,不允许喜欢其他人。
这是男孩父母最后的让步,王顺友也明白,他硬着头皮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向他们作了保证。
后来,王顺友在跟别人讲他的这次经历时,他总会高兴地补上那个结局:女孩大学毕业后,回到村子带着父母和男孩走出大山,两人如今已在成都定居结婚,事业小有成就。
也正是这次经历让王顺友明白,作为大山里的信使,他不仅仅要为大山送白纸黑字的信件,更多的是信件背后所代表的希望与光明。
那是外界亲人送来的叮嘱与祝福,是分居两地的爱人送来的温情与爱意,还有一所所大学送来的录取通知书。
而他,就是联结外界与这里唯一的纽带。
每年的录取通知书都是八月份下发,而这里的雨季也是八月,山洪暴发也多发于八月,但王顺友从没延迟过任何一个孩子的录取通知书。
这条“马班邮路”沿途四个乡,所有的录取通知书都是由王顺友脚踩泥坑,亲手送到。
他曾连滚带爬,浑身泥血交加地把两封录取通知书送到两个女孩面前,那信封上用塑料裹得严严实实,滴水未沾。
每当他看着一个个大山里的孩子走进高等学府,他都会感激自己的这份工作,让他亲眼看到即使是在这片荒凉贫乏的土地上,依然人才辈出。
他也曾在大雪漫天时,徒步趟雪10公里,只为了给姓陶的一家人送上十年未见的女儿的来信。
女儿在信中写道在外面有了新家,生了娃娃,生活幸福,陶家父母喜极而泣,王顺友也开心地流泪,他早已忘了翻过一座座雪山来时的寒冷和疲惫。
不知从几时开始,王顺友就不再是一个邮递员,而是化作了青藏高原上的青鸟,日日不停歇,只为这片土地送来吉祥和幸福。
木里藏族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处,这里没有路,没有电,不通电话,
为了让当地人能与外界保持联系,政府为当地的邮递员配了马,以马驮邮件成为了唯一信息传递方式,于是就有了“马班邮路”。
马班邮路有十几条,王顺友走的是最长的一条,也是最艰险的一条。
这班邮路全长近公里,王顺友走上一趟要花上14天,一个月他要走两趟,一年天,他要在路上待天。
图
源于纪录片《感动中国》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泥;
饿了吞几口糌粑面,渴了喝几口山泉水或啃几口冰块;
晚上蜷缩在山洞里、大树下或草丛中与马相伴而眠,如果赶上雨季,就得裹着雨衣在雨水中躺一夜,这个时候就没有穿过一件干衣服、睡过一个安稳觉。
同时,他还要随时准备迎接各种突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
年的雅砻江面上还没有桥,只有一条溜索。
王顺友像往常一样先把马寄养在江边一户人家,自己背上邮包,把绳索捆在腰上,搭上滑钩,向雅砻江对面滑去。
图
源于纪录片《感动中国》
然而就在快到对岸时,他身上挂在索道上的绳子断裂了,王顺友直接从两米多高的空中狠狠地摔下。
万幸的是他落在了沙滩上,可邮包却被甩进江里,江水湍急,邮包顺水漂去。
王顺友疯了一般,不识水性的他抓起一根树枝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江中,拼命地打捞邮包。
当邮包打捞上来后,王顺友像虚脱般瘫在地上,岸上的人说他傻,为了一个邮包,命都不要了。
他说:“邮包比我的命金贵!”
然而,这只是王顺友万千生死关的其中一个小坎。
他走的那条马班邮路有海拔米,零下十几度冰雪长覆的察尔瓦山,
图
源于《四川新闻联播》
有海拔米,气温却高达40度的雅砻江河谷,
有野兽常常出没的原始森林,
有十几座陡峭险峻的悬崖沟壑,
还有当地百姓闻之色变的“九十九道拐”。
年,雅砻江上的溜索换成了吊桥,王顺友能牵着马穿过这个江面了。
可前方的“九十九道拐”才最凶险。
这是一条盘旋着的羊肠小路,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江水,稍有不慎,连人带马都会被卷进急流之中。
王顺友每走到这处都会异常谨慎,就连马儿的步伐也小心试探着往前迈。
眼看就要走完“九十九道拐”,突然,一只山鸡飞出来,马儿吓得一个劲地乱踢,走在后面的王顺友刚上前拉住缰绳,慌乱的马抬起后脚踢在了王顺友的肚子上。
腹中巨疼难忍,王顺友倚着峭壁倒了下来,头上的汗水大颗大颗地下落。
图
源于电影《香巴拉信使》
当马儿终于安静下来后,看到主人痛苦的模样,它用嘴一下一下地蹭着王顺友的脸。
王顺友强忍疼痛,给它做了一个手势,以示安抚。
缓了一会,王顺友站起来,牵上马继续上路,一路上腹内疼痛加剧,他走走停停,实在忍不住就在地上躺会。
九天后,王顺友终于送完了这批邮件,那时的他已经疼得无法直立,邻居带他去县城检查。
医生说,由于耽搁太久,大肠已黏连破了三公分,再晚来两个小时,命都没了。
图
源于节目《人物》
做完手术后,王顺友保住了命,大肠却短了一截,肚子常常作痛,留下终身疾患。
这医院里待了45天,这是他一生中最长的假期。
出院三天后他又一次牵着马,在这条荒无人烟的马班邮路上,踽踽前行。
后来,有人问他为了这份工作搭上半条命,值得吗?
王顺友说:值得。他们一直在等着我带给他们消息,他们离不开我。
图
源于中国邮政报
王顺友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相依赖的关系。
山里没有盐,王顺友每次邮递前都会习惯性地在包里放一些盐巴,分给需要盐的居民;
他们只能用土方治病,王顺友就从外面带来常用的的感冒药;
他们很少吃到丰富多样的蔬菜,王顺友就往山里带去白菜、青菜、萝卜等许多蔬菜的种子,并教他们如何种植培育。
图
源于《川观》
在木里,没人不感激王顺友,是他让他们看到了大山之外的模样。
所以后来王顺友总是带着种子进山,带着当地人送给他的包裹回程,大包小包,鼓鼓囊囊。
有木里的特产,有烤熟的土豆栗子,也有他曾带到山里的那些种子长出的果实。
“每次一到地(居民家里),他们就像过年一样开心。”
所有人都喜欢王顺友,只有他的儿子除外。
王顺友的儿子王银海很厌恶父亲,他认为王顺友长年不在家,只会出门溜达,游山玩水,完全忘了家里的妻儿,尤其每次王顺友一回家都会带回一些食物,更显得王顺友在外面的日子很快活。
图
源于节目《人物》
直到王银海初二那年,父亲带着他走了一趟马班邮路。
一路上严寒酷热,悬崖江浪,原始森林里的猛兽,夜晚的“天为被、地为床”,王银海终于明白父亲为何整日在外“游玩”,仍是落了一身的病痛。
“我记得雪已经没过我的膝盖,我走了一段路,就感觉冷得打抖抖”。
当看到父亲把邮包的信一封封送到收信人手上后,他们的感激和喜悦也让他五味陈杂,他第一次感受到“马班邮路工作者”的伟大。
这次出行让王银海彻底与父亲和解,也让王顺友第一次感受到马班邮路上有人陪伴的滋味。
“苦和累我都不怕,就是怕孤独,这个日子不好过。”
王顺友在高原上奔波半生,伴他最久的只有一匹马,一壶酒,一个邮包,一条路。
“孤独的时候就要喝点酒壮胆,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有时候两三天也见不到一个人,走在大山里,一到晚上,就只有马和流星陪伴着我,其实很难过,喝了酒以后就什么也不怕了。”
图
源于节目《人物》
每次有记者去采访王顺友,他总是很高兴,不为名利,只是终于有人陪他走完这一程,那时的他总有说不完的话,唱不完的山歌。
而在大多数时间里,王顺友只能和马儿交流,他总会把马儿洗刷地干干净净,让它皮毛光亮。
自己每月块钱的工资,他会抽出块钱买马料。
路途艰辛,他哪怕累到腿脚抽筋也舍不得骑马,反而看到马儿太累时,卸下邮包自己扛着。
有时喝酒到尽兴时,还会笑眯眯地把酒壶递到马儿嘴边问它要不要喝上两口,马儿在此时就会蹭一蹭王顺友。
王顺友把马儿当作最亲密的伙伴,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内心的孤独寂寞,对家中妻子儿女的思念和愧疚,木里人赠与他的温情感动,他都会说给它听。
他习惯了和马相依而眠,习惯了走在那条邮路上,手上牵着马的缰绳。
40岁的王顺友背驼得很厉害,长年劳累留下各种病根,他在邮路上的行程开始拉长,但为了准时送达信件,他就缩短自己的睡觉时间,吃饭时间。
“我要走到走不动为止”王顺友成了马班邮路上走得年头最长的人。
年,木里通了公路,马班邮路在这里的历史彻底结束。
王顺友的儿子王银海接了父亲的班,穿上绿色制服,成为他们家里第三位邮递员,只不过这一次,他接过的是邮递车的钥匙。
他告诉父亲,从外面到木里,只需要开车两三个小时,王顺友开心地合不拢嘴,他想起曾有人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
“我希望能把木里的公路建设好,我们投递员能开着汽车送邮件,我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马班邮路乡邮员。”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王顺友用一生在马班邮路上,爱着大山那边的那群人。
图
源于《川观》
参考资料:
1.CCTV10《人物》——《感动中国之马班邮递员》
2.新华社《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3.《鲁豫有约十年故事之乡村邮递员》
文字为国馆读书原创,转载请联系作者
/
本文作者:糖味的橙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