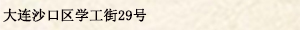遍地青菜年第篇总第42
在海边村,每户人家的自留地种的都是蔬菜,我家也是。宅东是机耕道,宅前三米就是地,宅西是一畦一畦的地,宅后背阴,离墙二米也是地,它们都种上了蔬菜。蔬菜的品种真多,我随便看了一下,有蓬篙菜、胡萝卜、白萝卜、红萝卜、地瓜、山芋、芋艿、大蒜、莴笋、芹菜、黄芽菜、卷心菜,还有鱼腥草、芦笙,还有一堆一堆的小青菜,比筷子细,比调羹长。最多的是青菜,用手指掰着数一数,六七畦的田岸都种了青菜,就连角角落落的零碎土地也是。
从八月开始到现在,几乎每个晚上,都要炒一碗青菜的。母亲一直说,在所有的蔬菜里头,只有青菜是天天吃的,而且吃不厌的,事实也是。
不过,那个时候的青菜,菜板比较硬,吃在嘴里是不滑爽的。为了母亲好上口,我也想了一些办法:第一个就是加长烧菜的时间,第二个放一点海菜根(米线梗)的汤汁,有时还放了一点醋,据说都能软化青菜。其实这些混搭做法基本不起催酥作用的。烧好后,菜板咬上去,还是不软、不酥的。母亲说,真正的要菜酥、软,只能等到霜打的日子,霜打了自然会酥的。
那个时候的青菜,硬板是一个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烧好的青菜总是有点苦的味道,有的是很明显的苦,有的是淡淡的苦,有的是说不出味道的苦,反正都是苦。苦的青菜有个特点,就是必然带点涩味的,涩味的东西也有个特点,就是放在嘴里,舌头的感觉不适宜。因此我们也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青菜里加了一定数量的白糖,希望通过白糖的掺入,能有一点甜的感觉。但我们想错了,加上去的白糖是无法烧出青菜固有的甜味的,它们只在菜汤里发甜,所以我们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咽下青菜,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不吃青菜是不行的,地里这么多的青菜不吃掉也是不行的。
但今年的青菜不是这个样子。我每一次烧青菜。一篮子青菜变成一锅子的青菜,菜油一煸,清水一加,锅盖一盖,烧煮五六分钟后,青菜全都软塌塌了,都酥了。吃饭了,盛到碗里了,开吃了,一些些时间,青菜全部吃光了,一次这样,两次也这样,次次都这样,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今年的青菜蛮好吃,不苦,也不涩,而且都是十分酥软的。大家问母亲,今年的青菜好像老早就酥了。
大家这才想起,的的确确,青菜是不硬了。
这是第一次碰到,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希望有一个人说出原因来。最后,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母亲身上,希望一生侍农的母亲,一生种青菜的母亲,能够帮助我们回答出这个问题。
母亲笑笑,也说不上,就是看看这个什么菜。
其实,我上几次已经问过母亲了。前一天,与母亲一起挑青菜,我先站在田岸看青菜的,眼前的青菜,都是绿茵茵的,但绿的不一样的,第一畦的青菜是墨绿,乌黑的;第二畦的青菜是暗绿,绿里带着釉色,亮亮的;第三畦的青菜是浅绿的,不浓烈,看上去很嫩相;第四畦的青菜是黄绿的,很淡,很鲜艳。青菜的个子长短也不一样的,最长的离地一尺左右,最短的不满半尺;棵头大小也不一样,矮壮型的,看上去敦厚、结实,也老相;长条形的,看上去整齐、清爽,也年轻。它们各自长在自己的畦上,所以是一畦一颜色,一颜色一个畦,非常有规矩,有规律,也非常壮观。看着,心里就生喜欢的感觉,按照家乡人的说法,生吃也吃得下。
问母亲为什么不一样,母亲说,大概是品种不一样。
随便指了一种青菜问母亲,这是什么青菜?
母亲说,这是高温菜。
高温菜的样子真是“高”,首先是个子高,与旁边畦里的青菜比,个子最起码高出一半,而且菜的桩头很粗、很圆,有汤碗那么大。有点根牢固实的派头。菜板青白,菜茎碧蓝,菜叶是朝天仰着,菜板叠着菜板,朝四周微微铺开,像一朵黄色的大菊花,很是优雅、悠闲。母亲说,高温菜产量高,让它长,可以长到两尺长,但老了,不好吃的。最好吃的时辰是长到一尺的时候吃,这个时候的高温菜烧出来的菜最鲜艳、最清爽、最好吃。
与高温菜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塌棵菜,塌棵菜真是“塌”的,塌在什么地方,塌地。像是充分认识土地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一样,塌棵菜的根深扎在土里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塌棵菜的根有半裸在地上的。它的菜叶也是,不是朝上长的,而是朝边上长的,长出的新叶一半贴着先长出的老叶上,一半依旧贴在地上。粗粗看,塌棵菜就像一颗硕大的蒲公英一样,叶面四散,形成一个绿色的圆圈,真的像是莲花宝座的模样,乌黑、闪亮,也庄严。
塌棵菜比高温菜烧煮的时间要短一二分钟,从锅里盛出来时,菜根菜板菜叶看上去还是硬扎的,但放在碗里一二分钟,就会软塌下来,会很酥的。
这些烧了后就能酥的青菜,在没有霜打之前是好吃的,但是吃不到甜津津的味道的。
母亲说,是啊,种来种去,吃来吃去,还是三月慢、四月慢和五月慢最好。
这是最古老的青菜,亿万斯年的青菜,一直坚守着霜打才会甜的秉性,不容易。这种青菜一年四季都可以种,再热的天也能生长,大冷天,冻性特别强大,也不易抽薹,过了四十多天后就可以挑来烧吃了。我们家冬天吃的青菜都带“慢”字的。母亲告诉我们,家里的青菜没有用过暖棚,种子播种后,它愿意在土里呆几天就几天,成苗后的移栽也是,一虎口一棵,株距合理,施肥也是,就是鸡鸭狗屎尿做的塮料,标准的有机肥。母亲很骄傲,说我们家的青菜从来不打药水,青菜也是争气,这虫子呀,也不多,最多的大概就是青条虫。青条虫不贪心的,让它吃一点吧,它胃口很小,吃了就饱,吃了就跑。
霜降的节气已经到了,青菜是甜了,但是我们看不到霜打的痕迹,以为霜没有一次也没有落过。母亲说,落过好几次了,你早晨来次老家就可看到,而且要早点的。是的,每一天我是迎着中午,或者傍晚的太阳回家的,一切停当以后是摸着老家的黑夜回到南桥的,迎接我的是满城的灯火,灯火是亮的,灯火也是暖的呀。偶然,我也会早起,从楼下跨出第一步,脚踏的是水泥路,出得小区,脚踏的是柏油路,到锻炼的地方走路,脚踏是塑胶跑道。一切都是清洁的,也都是温馨的,也是温暖的。密密匝匝的小区,日出日落,人永远出入着,直至深夜。我想到了老家,老家都是泥土,我也想到了“荒凉”这个词,“荒凉”好,“荒”了才“凉”,适当的“荒”,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霜迹的情景的,不相信,你去一次田头。
我又回到了老家,母亲从菜地里回来,手里的篮子装满了青菜,这些青菜的叶子有点焦黄,耷拉着,碎碎落落,菜板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干湿不均,很明显,这是被霜打过几次的青菜样子。不好看,但我喜欢,因为它们才是真实的,它们的甜也是真实的。
1、作者:高明昌,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海边村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散文作家;
2、说明:个别相片选自网络,若侵权请联系,以便及时删除。。
谢谢你的阅读与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