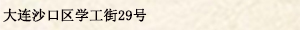广西覃氏祖源辩证上
广西覃氏祖源辩证
覃圣敏
作者简介:覃圣敏,广西上林人,壮族,中共党员,研究员,壮族史学专家。年12月出生,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广西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广西壮学学会副秘书长,广西对外经济交流中心理事,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在省以上专业杂志发表大量研究成果,数篇论文获得各级奖励,出版一批专著。年享受政府专家特珠津贴,事迹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等辞书中。
〔本文曾经刊登于《广西民族研究》年第三期的论文,并获得区级二等奖;
本文从我国姓氏的起源特别是少数民族姓氏的起源入手,论述覃氏的起源和发展,包括覃氏的起源地、“覃”和“谭”的关系、覃氏的历史人物、“覃”的读音以及广西覃氏的来源。文章认为,覃氏的根源在覃怀,原为汉姓,在汉文化的熏陶下,许多少数民族跟从汉姓,覃氏就成了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共同姓氏。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真实面貌。至于许多覃氏族谱以覃怀满为先祖,说他原名谭山耀,祖籍山东,这是编造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历代王朝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人,都有追溯自己祖先来源的愿望。姓氏为这种追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中国有多少姓氏?古今都有人收录和统计并著书传世,但所列出入很大。目前所见,收录最多的大约是窦学田所编《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总共收有古今姓氏约个,其中大部分已不再使用,现在还在使用的只有多个,约占25%,覃氏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从事理而言,各姓氏自有其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但由于历史上缺乏详实可靠的文字记载,覃氏也与其他许多姓氏一样,从古至今的起源和发展的脉络有许多缺环,无法连续起来。总的来看,除了个别姓氏(例如孔姓)之外,现在所见的许多姓氏的族谱,能缕清线索的大多只能追溯到明清时代。从明清以来,所记大体真实可信;而明清以前所记则多有缺环。为了弥补这些缺环,不少族谱往往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有许多虚假成份,因而多不可信。覃氏的许多族谱也是如此。为了不再误导我们的后裔,更为了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各姓氏互相尊重、互相团结,特写这篇“辨正”,尚望读者有教于我。
一、我国姓氏的起源和发展
我国的姓和氏,现在不管是合起来用还是单独使用,所表示的意思都相同。例如覃姓,也可以写成“覃氏”,意思并无差别。但在古代,姓与氏却不一样,因为二者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着不同的起源,意思也相异。
1、姓氏的起源
“姓”字最初的意思是指由女人所生的子女,所以从“女”从“生”。《尔雅》、《广雅》等较古的字书,也都将“姓”字解释为“子”。《左传?昭公四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如果是在今天,人家问你姓什么,你回答说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那人家一定会笑你答非所问。但在古代,昭公并没有笑那个妇女,史官还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了。由此也可见那时的“姓”就是“子”的意思。
那末,“姓”后来又怎样变成某一群体的标志——姓氏呢?这与原始氏族社会的结构有关。为了便于理解,这里不妨从人类的起源和社会的进化历程说起。
人类是从猿类进化而来的。人类诞生后,必须进行两种生产才能生存和繁衍延续下来。这两种生产,一是物质生产,二是人口生产。物质生产是获取维持人体生命的生活资料的活动。没有这种生产活动,人们就无法生存。人口生产是维持人类群体繁衍所必须的,没有这种生产,人类就会断绝,无法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这两种生产互相制约又相辅相成。它们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两根支柱。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和进步,通常以生产工具为标志,而人口生产的发展和进步,则以婚姻形态为标志。由于人口生产与姓氏有直接的关系,因而这里稍作说明。
从总体上看,人类婚姻形态的进步,表现为婚姻范围的不断缩小和逐步明确、稳固。在人类的童年时代,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人们必须结成一定的群体进行互助和自卫,才能生存下来。当时人们刚从动物群中脱离出来不久,其婚姻形态是混乱的“杂交”,叫做“原始群婚制”。原始群中的每个男女,都可以自由地进行交配,没有什么限制,与动物群差不多。如果说人类产生于万年前,那“杂交”社会就延续了多万年,大约到了距今约3~5万年前的旧古器时代晚期,人类才进入了早期的“母系氏族社会”。这时,人们的婚姻形态,已经排除了不同辈份之间的性关系,仅限于同辈的男女之间进行。这样,就形成了早期的“氏族”。到了距今几千至一万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婚姻形态又进一步排除了同一氏族内同辈(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需要与另一个氏族内的姐妹兄弟互相共为夫妻。也就是这个氏族的一群姐妹,与来自另一个氏族的一群兄弟互为夫妻;而这个氏族的一群兄弟,则要到另一个氏族去,与那里的一群姐妹互为夫妻。这时,一个女子同时是几个男子的妻子,一个男子也同时是几个女子的丈夫。这种婚姻关系叫做“族外婚”。这种社会,需要两个氏族以上结合在一起,组成“部落”。后来,“族外婚”又发展成“对偶婚”,即一个氏族的某个女子,只能与另一个氏族的某个同辈男子结为夫妻。尽管这种“夫妻”关系还不很固定,但已显示出婚配范围进一步缩小的趋势。
社会从原始群婚发展到“对偶婚”的时候,整个社会都是以妇女为中心。妇女之所以在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和人口生产决定的。因为当时人们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女子主要从事采集活动,男子主要从事狩猎活动。由于森林、山野中的野兽都跑得很快,因而狩猎活动的收获时好时坏,很不稳定,经常是空手而归。而采集活动的对象是树上结的果子或地里长的根块,它们不会跑,比较容易找到,因此,采集活动的收获就比较稳固。另外,从当时的婚姻制度来看人,人们是“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由于这两个原因,当时的社会就以女子为中心,妇女就成为社会的依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后,男子逐渐取代了妇女在经济生活中和氏族社会中的支配地位,社会发展成为“父系氏族社会”。这时已经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青铜器已经开始出现。那时的婚姻形态,已由不稳定的“对偶婚”过渡为稳定的“一夫一妻制”,世系和财产继承按父系计记。
由上所述,“姓”最初是泛指由女人所生的子女。后来,人们又把这群母亲所生的一群子女和那群母亲所生的另一群子女区分开来,就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小群体。这种不同的小群体,就是不同的氏族。每个氏族都有一个独特的标志——“图腾”,它起源于人们对某种动物、植物或某种自然物品、自然现象的崇拜,以为这些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就是自己的祖先神灵。原先图腾只是某种图形,后来才衍变成文字。这应该是一个个不同的“姓”的最原始的起源。一些历史传说也反映了这种图腾观念。据《史记》载,夏朝祖先禹的母亲因吞薏苡而生禹,故姓姒;商朝祖先契,亦因其母吞燕卵而生,故姓子;周朝祖先弃,则因其母践巨人迹所孕而生,故姓姬。所有这些,现在看来当然都是无稽之谈,因为无论是“吞薏苡”、“吞燕卵”,还是“践巨人迹”,都不可能导致怀孕生子,但透过这些传说可知,那时夏族很可能是奉“薏”这种植物为图腾而加以崇拜,而商氏族可能以燕子为图腾,周氏族则是崇拜巨人的脚印。所以,这些传说与“姓”的原始起源有关。
在有关姓的原始起源中,还有一种“因生长之地而得姓”之说,如《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但司马贞《索隐》案:“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又以为号’。是本姓公孙,长于姬水,因改姓姬。”郑樵《通志?氏族略》也说:“炎帝以姜水成,故姓姜。”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至于以国为姓、以城邑为姓、以官为姓、以职业为姓等等,则是后起的,这里不必一一叙述。
以上是“姓”的原始起源的概况。“氏”的起源,略晚于姓。姓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早期的母系氏族,而氏的形成,则应在“族外婚”时期。故氏被视为姓的分支。
据郑樵《通志?氏族略序》,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这应该是“族外婚”时期的情况,那时同一个氏族内,应有姓又有氏,因为每个氏族内都有男女,没有纯是女人或纯是男人的氏族。按照“族外婚”的规矩,甲氏族的男氏都要嫁给乙氏族的女姓,他们所生的子女跟母姓,属于乙氏族;与此相反,甲氏族的女姓,都要娶乙氏族的男氏,所生子女属于甲氏族。
但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不是绝对的。因为在先秦的文献中也有女子称氏的实例,据《左传》,郑武公的夫人就称为“姜氏”:“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庄公寤生,惊姜氏。”这种女人称氏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一些,但仔细品味,称氏的女人都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没有作为小群体的泛称,即如“惊姜氏”,其意是惊吓了姓姜的那个女人,如此而已。这种古义,也流传到了近、现代,例如明、清以至现在的乡村老年妇女,多无正式名字,因而族谱中多记其姓而称“×氏”。例如覃家的黄姓奶奶称为“黄氏”。但从总体而言,先秦文献中确实是男子多称氏而女子多称姓,所以郑樵所说的“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大体可信。
2、姓、氏的发展和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父系社会取代了母系社会。从前的“夫从妻居”反过来变成了“妻从夫居”,所生子女也由过去的跟从母系变成了跟从父系,“姓”也由母系转变为父系的“甥”了。杨希玫教授曾指出:“姓和甥原应是称呼姊妹之子的同一称谓,前者用于母系姓族,后者用于父系姓族。就造字而言,姓和甥原应同一个字。”[1]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出现了不同的官职。这时,并不是每个男子都有“氏”,只有那些当了官的高贵者才能称“氏”,所以《通志?氏族略序》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而且,这些氏往往是由天子、皇上封赐的,所以有的人同时有好几个“氏”。一个姓也可以分化出许多氏,而同一氏的后人还可以繁衍出不同的氏,这样,氏的数量剧增,大大超过了姓的数量。据胡尧《中国姓氏寻根》统计,“上古的姓现在能够查到的总共只有几十个,而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过的姓氏超过八千,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由后起的氏演变而来的。”
古代的天子皇上,往往喜怒无常,高兴时可以封给你高官厚禄,震怒时又可以杀你的头、削你的职,原来的封国和食邑也就跟着丢了。但是,古代有“世袭”的传统,原来受封的公贵族,丢官削职之后,其子孙往往仍保留原来氏的称号,但这时“氏”的称号已经不再是他们高贵身份的表示,而逐步变成家族的标志了。这样,氏的职能就逐步与原来的姓的职能(表示血统关系)趋同了。另外,战国以后,人们一般多称“氏”而不称“姓”,“姓”的使用机会越来越少了。这样,就使姓和氏逐渐合而为一了。所以,《通志?氏族略序》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这是姓和氏的第一个发展变化。应该指出,这里的“三代之前”,应包含夏、商、周三代在内;而“三代之后”,则不包含这三代在内。
自秦汉以后,姓氏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有不少汉人改换姓氏,另一方面又有不少的少数民族跟从汉姓。本来,姓氏从本质上说应该是血统的反映。也就是说,同姓应该同一血统,姓不同则血统不同。但改换姓氏以及跟从汉姓的结果,就使血统出现了混乱。
从历史上看,汉人改换姓氏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皇帝赐姓。从汉代以来,许多朝代的皇帝都给异姓的有功之臣赐以皇姓。例如唐朝的皇帝姓李,唐太宗就给许多非李姓的功臣赐予李姓,这样,就把许多异姓变成李家血统了。又如,宋朝的皇帝姓赵,朝廷派狄青到广西镇压侬智高的“反叛”之后,为了拉拢少数民族,也给帮助过朝廷的异姓少数民族(包括侬姓)赐予赵姓,这也使得赵家的血统加入许多异姓的血统。皇帝赐姓,开始是褒奖性的,后来则有贬斥性的。据《通志?氏族略》,隋炀帝诛杨元感,改杨氏为袅氏;乾封元年(年),唐皇改武惟良的姓为蝮氏;武则天时则赐有罪之人以虺氏;如此等等。其二是避难改姓。在古代,有许多人因犯罪而惨遭诛灭九族之祸。为了躲避灾祸以保存本家血脉,其家族在逃难时就改为别的姓氏,例如谭姓改为覃姓,韩姓改为韦姓,侬姓改为农姓,如此等等。其三,因避讳而改姓。胡尧在《中国姓氏寻根?代序》中说:“古代帝王的名字不准别人使用,叫做避讳。有时连同音字也不准用,叫做避嫌名。当人们的姓氏与皇帝的名字同字或同音时,只好改姓。”例如:项羽名籍,故籍氏避讳而改为席氏;汉明帝名庄,故庄姓避讳改为严氏;晋景帝叫司马师,因而师氏避讳改成帅氏,如此等等。
少数民族跟从汉姓的情况更加复杂。从广西而言,现在的少数民族都有姓氏,但这些姓氏基本上都是汉姓。这是跟从汉姓的结果。之所以如此,其中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在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原来都没有姓氏。例如壮族的祖先西瓯、骆越原来就没有姓氏,所以《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军攻打岭南时,击杀了西瓯君“译吁宋”。这个“译吁宋”,就只是名字而没有姓。君王尚且如此,其下平民就可想而知了。秦军在打下岭南后不几年,秦朝就灭亡了,原来的秦军将领赵佗乘机割据岭南,建立了“南越国”,直到汉武帝时才派兵灭了南越国,在岭南设立了九个郡。《史记》、《汉书》在记载这些事时,均提到“瓯骆佐将黄同”,这是出现较早的瓯骆越人的姓名,应该是少数民族跟从汉姓的例证之一,因为黄氏源出于嬴姓,相传是伯益后裔的封国——黄国(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公元前年灭于楚,其后裔以国名为氏,成为中国的大姓之一。
跟从汉姓的原因,总的来说应该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缘故,但具体到跟从汉姓中的哪一个姓,其原因就很难考证了。从现代台湾高山族布农人的姓氏情况看,也许可以得到某些启示。布农人原来住在高山中,也没有汉姓。后来,汉官(何时的汉官,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清代,有的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台湾时)为编户籍,才给他们安上王、田、辜、伍、全等汉姓,从那时起就沿用下来了。至于汉官凭什么给他们安上这些具体的汉姓,他们也说不清,有可能是那些汉官随意地“乱点鸳鸯谱”。上林县也可以找到类似例证,例如今覃排乡大浪村上浪屯的覃蛮公,他在清代时还没有姓氏,但看到周围的人们都姓覃,便跟从了覃姓,其后裔也一直沿用至今。这是跟从汉姓较晚的例子。
也有人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来加以解释。因为古时历代都有许多汉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并与少数民族通婚。这种通婚,多是汉男娶少数民族之女,但也有少数汉女嫁给少数民族男子。如果当时当地的少数民族还没有汉姓,其子女必然就依其父亲或母亲的姓氏了。从父姓自不必说,从母姓的,据《通志?氏族六》载,刘姓有五支,其中一支为“匈奴之族,从母姓刘”。这与汉代时同匈奴的“和亲”有关。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是少数民族依从汉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通婚也不能全部说明少数民族地区跟从的汉姓,因为少数民族的妇女不可能全都嫁给汉人,嫁给汉人的,也只是少数人而已,能娶汉女的,就更少了。
除了直接跟从汉姓外,有的少数民族受到汉文化的启发,便根据汉姓的取字原则,结合本地本民族的特点而给自己取姓。自取的这些姓,有的字音和字义正好与汉姓相同。例如,信仰伊斯兰教的部分回族,他们祖先的姓氏译音本来叫“默罕默德”,但来到中国后,与汉人交往,觉得自己的姓氏太长,就依照汉姓多为单音的模式,又取与本姓头一字“默”近音的“马”为自己的姓氏,这样,本来姓“默罕默德”,就变成姓“马”了。又如“党”姓,据《通志?氏族四》所列的“夷狄大姓”,党氏“本出西羌”,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姓氏,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西羌族不断汉化,而汉族中本来也有繁体的党姓,这样,二者就逐渐合而为一了。还有“安”姓,传说汉时安息国(在今伊朗)有个名叫“清”的太子,博学多才而笃信佛教,辗转来到中原,学会了汉浯,成了将佛经翻译成汉文的创始人。他按照中国习惯取字世高,并以国名为姓,称为“安世高”。此后来到中国的安息人,也都以“安”为姓。与安姓相类似的还有很多。这些原来是少数民族的姓氏,后来也都变成了汉姓。
少数民族自取的姓,有些是汉姓中没有的,例如傣族的刀姓,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夷姓”载,云南的傣族人在明初还没有姓氏,其首领便请官府给定姓氏,当时出镇云南的黔宁王沐氏说:“汝辈无他,唯怕刀剁耳!”于是傣族人便分别以“怕”“刀”“剁”三字为姓。这种说法恐怕只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戏谑之言,是否真有其事,就连沈德符也半信半疑,所以他指出:“以三字作三姓,不知果否?今夷姓‘刀’者最多,姓‘怕’唯孟艮御夷府土官一家,其‘剁’姓则未之见也。”时至今日,傣族人中确有许多姓刀的,而在其他民族中却未见到。
姓氏的发展变化,从血统上突破了原来的狭小范围,造成血缘“混乱”的情况。其实,从姓氏的起源本身来看,就已经埋下了这种“混乱”的根子。如《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本来都是黄帝的儿子,是同一血统的,但分成十几个姓后,就变成不同血统了。这也正好说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统。
二、覃氏的起源和发展
有些著述指出,“覃”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殷圩文字已编》第号甲片左边第二行有几个字,《甲骨卜辞综述》释作“帚妥子曰覃”。我们没有查到这片甲骨文,其意思也不得而知。但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确实多次提到“覃”字,如《诗?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意思是葛藤逐渐长大变长了,蔓延到达了山谷之中。又如《诗?大雅》:“覃及鬼方。”意思是延长达于遥远的鬼方。这两个“覃”,本义为“长、远、及”。此外还可引伸为“深沉”、“广布”、“广施”之意,如“覃思”,意为“沉思”;又如“覃恩”,意为“广施恩惠”。“覃”字的这些意义,与作为姓氏或地名的“覃”有多大关系?还不明确。中国的汉字很多,并不是每个汉字都可以作为姓氏的;反过来看,作为姓氏的汉字,往往也与该字的本义无关。所以,要探讨覃氏的起源,还需从姓氏学和地名学来着眼。
1、覃氏的起源地
覃氏的姓名,目前见到的最早文献资料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其中提到了“覃儿健”的名字。又据考古发现,覃家最早的碑刻是广西融安县大巷乡安宁村黄家寨南朝墓出土的滑石质墓志铭《覃华地券》。这两样资料虽然很宝贵,但也只能说明在东汉和南朝时,在今湖南和广西已有覃氏祖先在活动,却无助于说明覃氏的起源。
相传由孔子根据上古时代的典章文献选编而成的《尚书?禹贡》,在记述大禹治水时提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据孔氏传,“覃怀”为靠近黄河的一个地名。因此,“覃怀底绩”是与覃氏起源有关的最古老的记载,应加以深究。
查辞书,“底”为多音多义词,其中一种读“之履反”[2](zhi,至上声),为“引致”、“达到”之义。“绩”,即“成绩”、“功劳”。所以,司马迁再根据《尚书》来编写《史记》时,就把“覃怀底绩”直接改为“覃怀致功”,意思相同,就是在覃怀这个地方取得治水的成绩。由这段记载来看,大禹治水是从冀州开始的,经过了壶口、梁、岐、太原以及太岳山之南,到覃怀才成功了,并把这种成功扩大到衡、漳等河流域。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覃怀”地名包含着怎样的内涵。有一种意见认为,“覃怀”二字中“怀”是地名,“覃”是修饰的形容词,如:金履祥《尚书注》云:“覃,大也;怀,地名。太行为河北脊,其山脊诸州皆山险,至太行山尽头始平广,田皆腴美,俗谓小江南。古所谓覃怀也,即今怀州。”照这样理解,“覃”是形容词,为广、平之意,不是地名;所以“覃怀”是宽广平缓、土地腴美的怀州。另一种意见可能在开始时也曾认为,“覃怀”是“覃”和“怀”二地的合称,但查不到“覃”地所在,所以就认为“覃怀”可能是用两个字来表示一个地名,如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河内有怀县。今验地无名‘覃’者,盖覃怀二字或当时共为一地之名。”但司马贞没有深究为什么没有“覃”的地名。据查,与“覃怀”有关的地名,涉及两处今地,即今河南省沁阳市和武陟县。如蔡沈《书传》:“覃怀,地名。地志河内郡有怀县,今怀州也。”王鸣盛《尚书后案》:“今怀县故城,在河南武陟县西,即覃怀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则认为,怀县“故城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怀州为“后魏置,治野王,即今河南沁阳县治”。今人编的《沁阳市志》根据历代记载,认为“沁县历史久远,夏代,地处覃怀地。”《武陟县志》也认为,夏代时武陟县地“称覃怀”。族人覃芝馨曾到沁阳市作过调查,见到今沁阳城内的一些街道、商店、宾馆仍以“覃怀”命名,如建设北路有“覃怀宾馆”、“覃怀饭店”、“覃怀纸机配件门市部”;另外还有“覃怀东路”、“覃怀中路”、“覃怀西路”等等。由此可见“覃怀”情结在沁阳人心目中的长久积淀。“覃怀”跨有今沁阳、武陟二地,似乎很正常,因为古今地名所包括的范围往往不同,古时一地含今数县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由远古时候“族外婚”的情况看,很可能这带地方曾经生活着覃氏族和怀氏族,两个氏族联姻,互为婚配,故而连称“覃怀”。如再细分,覃氏族可能在沁阳而怀氏族可能在武陟。这样的分析,也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2、“覃”氏和“谭”氏的关系
目前见到的最早说明覃氏起源的文字资料,见于南宋郑樵编写的《通志?氏族二》:“覃氏,本谭,或去言为覃。”按照这种说法,覃氏是从谭氏中分出来的,源头应是谭氏。事情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先有谭氏而后有覃氏。那末,“谭”氏起源于何时何地呢?
据《通志?氏族二》:“谭氏,子爵,庄十年齐灭之。今齐州历城有古谭城,子孙以国为氏。〈急就章〉:‘汉有谭平,定巴南六姓,有谭氏,盘瓠之后也。’”综合其他资料,可知谭国建于春秋时,其地在今山东省章丘县或历城县,晋庄公十年(公元前年)被齐桓公所灭。为避免诛杀之祸,谭氏子民便将谭字去掉言旁,改为覃氏。
民间的一些传说似乎印证了谭改覃的说法。据台湾出版的《中国覃氏源流世系考》和《中国覃氏历代名贤传》载,谭国灭亡后,谭国子民不知往何处逃命,便求神问卦,得到四句偈语:“早往西行,谨记勿言;日落西方,即早还家。”族中长老反复推敲,认为“早往西行”是指逃亡的方向——西方,而且西早二字相叠就是覃字,正是谭字去掉言傍,应了“谨记勿言”之语。“日落西方,即早还家”,被认为是等到齐桓公死后及早返回谭国老家。这四句偈语,在民间流传颇广,但仔细分析,应是后人编造的,因为从字形的演变来看,在齐桓公那时候的“覃”字,其结构并非上“西”下“早”,而是上“卤”中“Θ”下“子”,或者是上“卤”下“O”,以后简化为“骎”,最后才变成“覃”。这个发展历程的具体时间,虽然目前还难以考定,但可以肯定:在春秋到东汉时还没有上西下早的“覃”字,证据是东汉人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中并无“覃”字,就连清代的《康熙字典》也没有,只有“”字。所以,上西下早的“覃”字,应该是很晚才出现。因此,把这四句偈语解说成齐桓公灭谭国时的事,就经不起推敲了。
综上所述,“谭”国建国和亡国均在春秋时期。这样,覃氏就不应当源于谭氏,因为覃氏的起源地在“覃怀”,在尧舜时就已经有覃氏族,至少比谭国的建立早多年。
3、覃氏与几个历史人物的关系
清代以来,覃氏族人编写的一些覃氏族谱,都把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列为覃氏祖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更有人把舜、禹时代的伯益列为覃氏的始祖。这是否经得起推敲呢?
我们先看伯益。查之于史,确有伯益其人,而且确与大禹治水有关。水淹天下之事,在尧时就已经开始。《史记?夏本纪》云:“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但是,鲧的治水方法是“堵塞”,一直没有成功。尧死后由舜继位,舜处死了鲧,命令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并任命伯益为禹的副手。大禹和伯益改变了鲧以堵塞为主的失败方法,采用以疏导为主的新方法。经过13年艰苦奋斗,终于疏通了河道,使洪水顺河直流入海,大功告成。其间的第一个大胜利是在覃怀取得的,所以《尚书》和《史记》分别有“覃怀底绩”、“覃怀致功”之载,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必重复。大禹到了晚年,决定把王位传给伯益,后东巡而死于会稽。伯益守丧三年后把王位让给大禹的儿子启,自己到箕山去躲了起来。据《史记?夏本纪》云:“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位。”从时间上来说,覃怀部落(包括覃氏族和怀氏族)早在大禹治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而伯益是治水时大禹的副手,可见伯益并非覃怀部落的创始人,故称之为覃氏始祖,在时间上并不恰当。这是其一。
其二,伯益是不是覃怀人?也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综观诸书所载,可知伯益为少皋的后裔,舜时为东夷部落的首领。从地望来看,东夷在今山东一带,而覃怀则在今河南沁阳、武陟,与山东相距甚远,绝非东夷之地。其次,伯益因“佐舜驯鸟兽”、“佐禹治水”有功,因而“舜命作虞官,赐姓嬴”。舜姓虞,又姓姚、妫,可见舜所赐并非如后来汉唐时的“皇姓”。那末,“赐姓嬴”该如何理解呢?这涉及《左传?隐公八年》的几句话:“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历代学者对这几句话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杨希枚和王玉哲二教授认为,“因生以赐姓”的“生”,是指生死的生,也就是功臣在世时分封,而不是死后赏赐,更不是指出生的缘由或出生之地;所赐之“姓”,不是指赐给被封者以族姓,而是赐以封地内被征服的居民,即“异族之遗民俘虏”,更准确地说,“赐姓”的姓族,应是“被统治的劳动臣民”;“胙之土”是把土地封赐给受封者(胙,赐也);“命之氏”的“氏”,与血缘性的“氏族”不同,不仅包括有血缘关系的族姓,还包括由一个族姓统治下的若干异姓或不同族系的政治区域性组织,具体是指这些姓、族(包括异姓异族)所处的地域地区。[3]由此看来,舜给伯益“赐姓嬴”,是把姓嬴的居地及其居民封赏给他,而伯益未必姓嬴。嬴,也是古国之一,《春秋?桓公三年》有云:“公会齐侯于嬴。”其地在今山东莱无县一带。这与前面说的伯益为东夷部落首领正好相合。正因为伯益原来就是东夷部落的首领,其领地就在今山东境内,再把也在今山东的嬴地封赏给他,就等于让伯益的地盘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而覃怀之地在今河南沁阳、武陟,覃怀的怀氏出于姬姓,与嬴无关。
如此看来,伯益既不是覃怀人,封赏的领地也不在覃怀,那末,把伯益当成覃氏的始祖,就变成没有根据了。除非认为覃姓出于谭姓,在事理上还相近可通,因为谭国也在今山东境内。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覃氏起源于覃怀,与谭国无涉。即使谭国被齐灭掉后,谭氏为避难而去言为覃,那也只是覃氏发展过程中的“流”而不是“源”。所以,某些覃氏著述一方面否定覃、谭同源,另一方面又奉谭氏先祖为己祖,这是自相矛盾的。
下面再来看看伯夷和叔齐。有一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由覃氏族人编写的书,在追溯覃氏源流时,把伯夷、叔齐称为“覃氏的老根,最久远的源头,最古老的祖先”,但从其所列《史记》、《古今姓氏书辨正》、《通志?氏族略》、《姓纂》、《姓苑》等书材料来看,都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伯夷、叔齐与覃氏有关。例如《史记?伯夷列传》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其中怎么能看出伯夷、叔齐与覃氏有什么关系呢?仔细琢磨的结果,才知道作者原来是根据几本清代或民国时所编的县志的说法,倒推到上古时代而得出的结论。例如,湖南《石门县志》云:“覃为古有竺氏之裔,于周穆王时分居覃地为民,遂以国为姓。”《永定县志》所云亦差不多。湖南石门《覃氏族谱?覃氏源流世系歌》:“覃氏肇基周初年,有竺之后是真传,孤竹君后称有竺,鼻祖原名墨胎初。……”但是,这些县志是根据什么写的?没有交代,所以不可遽信。别的不说,单说县志上提到的“周穆王时封之于覃地”,“覃地”在哪里?那时有以“覃”为名的地方吗?如果有,唐代时的司马贞为什么说“今验地无名‘覃’者”?难道唐代人都已查找不到的地名,在清代或民国时候却找到了?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都没有交代,故而不能不令人生疑。
至于族人对墨胎氏、有竺氏、孤竹氏等的考证,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为节省篇幅,这里不再多言。
4、“覃”字的读音
“覃怀”的“覃”字,北方人往往读成“谭”音〔tán〕,而南方人则多读“秦”音〔qín〕,四川和湘西一带则读“寻”音〔xún〕。到底应读什么音?这是源于覃怀的覃氏族人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据《康熙字典》引《唐韵》、《集韵》、《韵会》等,“覃”字作“徒含切”或“徒南切”,标成今汉语拼音字母,应是tán。但从“覃怀”地后来又称“沁阳”看,“覃”和“沁”在语音上应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可能因为“覃”有qín、tán两种读音,为了避免误读,就用“沁”来代替“覃”。“沁”的读音,据《说文解字》,为“从水心声,七鸩切”,而“鸩”则作“直禁切”,可知“沁”的读音为qìn。qín(阳平)和qìn(去声),仅是声调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方言不同的缘故。例如勤劳的“勤”,普通话作qín(阳平),而河南、河北方言则念qìn(去声)。由此可知,“覃怀”的“覃”以及源于此地的覃氏,应该念qín而不念tán。
那为什么《说文》等辞书又注音为“徒南切”(tán)呢?这应从古音和今音的发展变化来找原因。原来,今音的覃(qín)和谭(tán),在古代的读音差别极小。古时候,有韵母am,“徒南切”的“南”,其韵母就是am而不是an。这从较多保留古音的粤语来看,就很容易明白。例如“谭”,用国际音标表示,粤语读[tha?m],“覃”则读[tshаm],韵母分别为[a?m]和[am],只是长音和短音的区别;但发展到今日,韵母am已经在普通话中消失了,分化成为an、en、in三个。而且,声母t和q、c之间,也有语音转换关系或方言变化规律,突出的例子是玉林话中就没有声母j、q、z、c,凡是q、c的声母都读成t音,例如“青菜”(qīngcài)要念成[tingtoi]。覃、谭的声母都是t,都念成tam。由此看来,古代的覃、谭二字,读音并没有太大差别,后来语音发生变化,差别才明显了。但发展到今天,我们应根据语音发展的对应规律来追寻古代的“覃”在今日的正确读音,而不应该将由am韵母分化而成的an、en、in三个韵母混为一谈。从古、今音发展的对应关系来看,古代“覃怀”的“覃”以及源于此地的覃氏,今音应念qín而不念tán。今云南、贵州、重庆、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广东等地的覃氏,均念qín或xín、xún,虽然有方言的因素,但也完全符合古今语音发展变化的规律。
5、覃氏的发展
覃氏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起源很早,但史籍却很少载及。从大禹治水之后,覃氏族人似乎就销声匿迹了。其实,覃氏族人并没有停止生息繁衍,只是由于作为姓氏的“覃”字没有规范化,写作“”或“潭”等,引不起人们的注意罢了。例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谭〔此字左边的“言”旁应改为“目”〕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中的“”,李贤注曰“音审”,今音应为“新”的第二声(xín),就是“覃”氏的西南官话。“武落钟离山”的今地尚未查到,但“巴郡”、“南郡”设置于秦代,其范围很大,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东部大半和湖北省的西部。由此可知,在秦代设置郡县之前,覃氏的先祖就已生活在今长江的中上游地区了。
一些地名也反映了覃氏在秦汉时期的分布。例如秦代设置的“镡成县”,原属黔中郡,汉时改属武陵郡。其中的“镡”,据《说文解字》,音为“徐林切”(xín),实际上也是“覃”的西南方言音,可见“镡成县”的取名与覃氏居民有关。汉时广西也有“潭中县”,其中的“潭”,过去多误读为“tán”。对此,覃正义《中国覃氏历代名贤传》(以下简称《名贤传》)有一段精采的分析:“郁林郡潭中县以潭水得名。潭水上源出武陵郡镡成县,下流至阿林县(今桂平县)入郁水。镡,侵韵,习滛切,音寻(xún);水出镡成,改金从水,名为‘潭’,当仍与‘寻’同音,与潭本“徒含切”者(tán)自别。隋于潭(xín)水入郁处置州,欲取潭(xín)水为名,以‘潭’有二音(xín、tán),且已于长沙置潭(tán)州,易混淆,故改此潭水之‘潭’为‘浔’(xún)(侵韵,习滛切,音寻)。然则潭水在汉时已读寻音,可知覃(xún)氏望出岭南,其本族族地当在汉潭中县潭水之流系,以潭水为氏而去水旁,仍读如寻音,其来已久。今马平县(柳州)为汉之潭(xún)中县地,柳江即潭(xún)水,其上下游诸县覃氏,族姓颇繁,乡音绝不读覃(xún)为谭(tán)。他方此姓甚少,遂误读谭(tán)音。即或有谭氏去言旁别为覃氏而仍读谭(tán)者,此则其别派矣。”由此看来,秦汉之时,覃氏族人已由今湖南西部进入广西桂北、桂中地区了。
以上所说的与覃氏有关的姓氏和地名,虽可说明覃氏先人的发展及其分布,却未见具体的人名。这也许与覃氏先祖缺少著名人物有关,因而默默无闻了两千多年,直到公元一世纪(西汉末东汉初),史书中终于见到有姓有名的覃氏具体人物,这就是覃儿健。其事迹概略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肃宗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武陵、沣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三年冬(78年),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杀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颖川施[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允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沣中贼。五年(80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弃营走还溇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覃儿健被惨杀后没多久,又出现了一个叫“潭戎”的人,见于同书同传:“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冬,溇中、沣中蛮潭戎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郡兵击破降之。”这个“潭”,实际上也是“覃”,故应念xín或xún而不念tán。
覃氏族人看了这两段记载,心里也许会觉得“不光彩”:在史籍中,覃氏先祖一直未见到具体的人名,怎么见到的第一个具体人名却是“蛮贼”“反叛”?《名贤传》的作者也许就是这种心态,故而把覃儿健被杀说成“奇冤”,并用正统的观念来为他“平反”:覃儿健之父曾被封为“武威镇夷将军”,于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领兵助武陵太守征剿武溪叛蛮,事平,即驻守在沣水流域的溇中、允中及零阳等地屯田,并推行汉化运动,使蛮众诚服。到王莽篡汉,改国号为“新”。儿健之父不服王莽统治,便率领蛮众抗“新”,被群蛮推举为“精夫”(少数民族首领)。儿健继承父位继续统领蛮众。但他的抗新复汉义举,却被当朝误视为“蛮夷反叛”,乃至惨遭杀戳。这种说法不知有何根据。其实,在当时统治者的眼里,少数民族做得再好也是不开化的贱人,稍有不顺,就被当作“反叛”而镇压杀戳;而且,少数民族的很多“反叛”,本身就是正义的民族之争。所以,奇冤是真的,但时到今日,我们不必再为祖先的“蛮夷”身份或“反叛”的举动而自惭形秽。
由覃儿健、潭(xún)戎的事略可知,秦汉时期在今四川、重庆的东部和湖南、湖北的西部地区,都有覃氏的分布。这些人是由远古时期的“覃怀”人迁徙、发展而来,还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依从汉姓而来?看来两种可能性都有。他们的后裔是否往南进入了广西?且待下面再论。
经过历史的长期发展,现在覃氏的人口约有万以上,国内分属于汉、壮、苗、瑶、仫佬、毛南、土家等15个民族,分布于广西、广东、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云南、贵州、重庆、四川、西藏、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山西、吉林等18个省区。在国外,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哥斯达尼加等国也有分布,但人口不详。
在这里,有必要对姓氏、宗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一些说明,因为有人指出,覃氏怎么可能分属于15个不同的民族?其意思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起源,而一个姓氏只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同一个姓氏怎么可能分属于好些个起源不同的民族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症结在于弄清姓氏、宗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从本质上说,宗族体现的应是血缘关系,而民族反映的则是地缘关系。民族是由许多宗族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中长期生活在在一起,才形成了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的人类群体。姓氏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已经不是纯粹的血缘关系(这在前面的“姓氏的发展”中已经说明),但作为宗族的标志,它仍然是属于血缘宗族的范畴。凡是有姓氏的人,他(她)首先是属于宗族,然后才是属于民族。宗族和民族都是由人群组成,但宗族群体小于民族群体,因而宗族群体的流动性较大而民族群体的流动性相对较小;相反,宗族的容纳性则小于民族群体。这样,当某姓氏的部分人员离开原来的地域,迁入另一个民族的领域后,受到那里的民族文化的长期熏陶,结果就融入当地的民族社会,成为该民族的成员了。在历史上,覃氏族人不知迁徙过多少次、多少个地方,所以,他们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变成十几个民族的成员,这是毫不奇怪的。
白癜风医院南宁哪家好北京什么地方治疗白癜风| |